研究专题
新马大众文化资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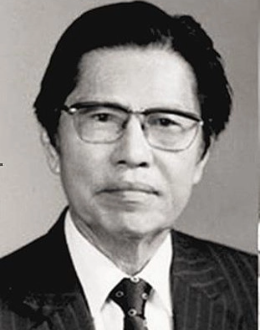
“跨界”文化人:蔡文玄、苏莱曼和柳北岸的故事
叶舒瑜
柳北岸(1905-1995)是新加坡著名诗人,原名蔡文玄。原籍广东潮安,父亲在他三岁时离世,此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蔡氏家族几代人都是经营织布厂的,但后来面临进口洋布的竞争,生意每况愈下。随后他们转而投资蜜柑为生,然而缺乏专门的知识与管理经验,收成并不理想,不得已向亲戚借贷大笔资金以维持生意。根据家族编纂的族谱,蔡文玄的祖先最初居住在河南。由于战争,他们迁往安徽,然后移居福建(莆田的兴化),最后在明朝时期,他们选择在广东定居。蔡文玄来自书香世家,他记得自己的祖辈曾通过科举获得进士,并在嘉靖年间被明朝皇帝任命为云南道江西巡按监察御史,因此他们一家在石门村里备受尊敬。
1. 与东南亚结缘,先后从事教育、开设画室以及编辑工作
学业有成的蔡文玄先是加入国民党宣传部担任艺术部股长。当时,他的月薪55元,主要负责写文章(也包括会议记录)、整理国民党内名人语录、设计宣传材料(例如海报与标语等)和处理任何与军队相关的后勤工作。这对蔡文玄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而且这笔薪水不但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还可以让他随军队免费游历中国的山川美景。1927年,退出国民党的蔡文玄决定陪同他的四哥前往新加坡,并接下了位于柔佛大同学校的教职。一开始,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然而他过于“新派”的教学方法引起校董们的反对。最终他放弃了教书,返回新加坡从事绘画的工作。1929年,他与朋友林龙在新加坡的当店巷(克力路)成立画室,而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正是新马广告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在新加坡至少有20家公司主要从事广告制作以及行销宣传。
对于成立画室,蔡文玄最初是相当有自信的,他知道如何将图片放大或缩小,如何快速制作高质量的广告、大型海报及户外广告等。为了方便介绍自己画室的作品,蔡文玄也购买了一台柯达相机为画室的作品拍照,以此展示给客户观赏。他最早的客户包括联源影片公司的经理殷宴,他也是爱同小学的前校长。爱同小学成立于1912年,并由福建会馆出资创办。由于蔡文玄也曾是教育工作者,这使得他更容易取得殷宴的信任。后来,蔡文玄的前同事亦为他引荐联和影片公司的经理周海滨。同时,因为蔡文玄的画室临近南海影片公司,相信他在招揽顾客时也有可能向南海的经理黄敬一推销过画室的服务[1] 。据蔡文玄的回忆,他的画室生意稳定,每个月从绘制广告牌、印刷海报和制作广告幻灯片等工作可赚取的净利润约为120至150元。如果他与林龙平分收入,每个人至少可以得到60至75元,这比当时任何一家普通印刷公司职员每月20元的工资还要高出许多[2]。蔡文玄也写得一手好书法,相信在制作广告与海报时亦可派上用场,战后邵氏出品的电影片名及海报、公司招牌、本地作家方北方、韩玉珍等人的书名题字,便采用蔡文玄的书法,其纤细雅致的字体更是独树一帜。
后来,蔡文玄的合伙人林龙决定出售自己的股份,并利用这笔钱回国筹备婚礼。对蔡文玄而言,独自一人撑起画室的所有工作是个挑战,因此他决定改为邵氏兄弟打工。他当时领取的薪水是每月75元,工作内容包括写信兼任秘书、设计广告和电影海报等。他同时也需在晚间协助邵氏兄弟打理华英戏院的门票与收入[3] 。在公司里,邵逸夫只雇用了一位打字员、一位快递员、一位电影操作员和两位负责财务和会计的经理。当时邵氏兄弟租下的办公单位分隔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则被海峡华人曾几生的南华贸易公司所占用,而曾几生(1896–1929)与蔡文玄同为潮州人,沟通上毫无隔阂[4]。前者除了创办南华贸易公司,也是电影业的翘楚,该公司主要发行来自上海的国语默片,并在中华戏院上映这一系列影片。曾几生1896年出生于新加坡,他的父亲乃“马来亚西米大王”,后来他也继承父亲的万振美西米生意。曾几生的父亲曾汝平(1863-1937)祖籍广东潮安,并在新加坡投资靠种植甘蔗和胡椒致富[ 5]。他热心教育,常定期捐款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例如1926年,他在潮安骊塘出资创办了一所学校,命名为务滋学校,也曾捐款给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添置藏书,当时的校长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学校的图书馆。曾几生通过他的南华贸易公司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该公司以进口中国制造的“和合粉”味精而闻名。除了支持并响应国货运动,曾几生于1920年与王萃琛、李岳生、陈楚书、陈海澄、卢松兴、陆馥涯、廖统伟、蔡辉生、许复起和黎宽裕等人一同创立了青年励志社,是推动本地白话戏剧以及其他文艺活动的重要文化组织[6]。
由于身体不适,蔡文玄在1930年初辞去邵氏兄弟的职务,回到中国养病。随着日军的铁骑南下,蔡文玄决定再次前往新加坡寻找工作,并尽快把家人接过来当地避难。1937年,蔡文玄独自抵达新加坡,会见了邵仁枚和邵逸夫。虽然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0元,但是他还是答应担任邵氏兄弟的秘书兼《电影圈》的编辑。为了增加收入,蔡文玄也在工作之余为学生补习,并在隔年将妻子、孩子和保姆顺利接到新加坡,一家团聚。蔡文玄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的庞大开销,他的妻子便在新民小学教书,而该小学也为所有教职员工提供宿舍,这替他们省下了一部分住宿的开支。后来,蔡文玄也凭着自己出色的表现,成功说服老板将他的工资提高到每月100元。随着他的孩子进入新民小学就读,他们一家五口的生活日渐稳定。
2. 成为邵氏马来电影制片厂的“隐形编剧”
二战结束后,邵氏重新投入电影发行与制作,并推出《娱乐》小报委托蔡文玄负责督印。这份小报创刊于1945年12月19日,每逢周三和周六出版,价格仅为每份一分钱,主要目的是为邵氏在新加坡放映的电影做宣传。尽管如此,蔡文玄并没有忘记电影能结合教育和娱乐大众的目的,这是他编辑《电影圈》和《娱乐》时采取的方针,也成为他为邵氏撰写马来电影剧本时的创作动机。在马来电影制片厂(Malay Film Productions Limited)出品的众多马来电影中,《Kerana Kau》(1953年)、《Sri Menanti》(1958年), 《Ribut》(1956年), 《Taufan》(1957年), 《Bujang Lapok》(1957年)和《Masharakat Pinchang》(1958年)的原创故事皆由蔡文玄负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每部电影的片头得到印证[7]。偶尔在报纸或宣传材料中介绍这几部电影时,文中也会提起蔡文玄或是他的笔名柳北岸,例如《南国电影》在宣传《Masharakat Pinchang》时便曾报道此事。其他电影如《Patah Hati》(1952年), 《Panggilan Pulau》(1954年), 《Bernoda》(1956年), 《Belantara》(1957年)和《Kembali Saorang》(1957年)等也可能出自蔡文玄,尽管这几部电影片头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从他遗留下来的中文电影手稿(剧本),笔者猜测邵氏兄弟很有可能曾将他的故事大纲,转告负责拍摄的马来或印度导演作为参考。虽然最后拍摄完成的马来电影和蔡文玄手中的剧本有出入,但在某些重要情节上还是有相似之处。
蔡文玄为马来电影制片厂撰写了超过十个电影剧本,而所有剧本首先是以中文完成,然后提交给邵氏兄弟做出最终的定夺。一旦批准,这些剧本将被送去翻译,并在拍摄现场分发给演员和导演,以便他们在拍摄时可以了解电影内容并进行即兴创作。蔡文玄曾提到,每次撰写一份剧本需要至少一至两万字,如此才能够为电影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与详细内容。他也坚信在银幕上所呈现的故事情节必须要引起观众的共鸣。至于如何引起共鸣,蔡文玄在自己的访谈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事实上,每位导演都有责任决定如何呈现剧本里的每个场景与情节。在进行内部审查时,例如检查电影毛片(即正片的拷贝)以及故事的连贯性时,一旦发现问题,蔡文玄也会在此时对拷贝进行小幅度的剪辑或修饰。由此可见,蔡文玄对电影制作的各个阶段都了如指掌,但他更关心的始终是电影内容是否具有意义。
蔡文玄在为马来电影制片厂撰写剧本或筛选作品时,一般会倾向选用马来民间故事,毕竟熟悉的题材较容易迎合观众的口味。他也尽量避免触及可能冒犯马来观众的敏感课题,也曾参考西方文学经典,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他认为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往往更能成功获得马来观众的喜爱。蔡文玄在撰写剧本之前对古兰经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与阅读,也为自己取名苏莱曼(Sulaiman)。他知道古兰经是一部重要的宗教典籍,也是指引回教徒在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规范依据。偶尔,他也会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找寻灵感,例如《Roh Membela》(1955年)中的男主角类似刚正不阿的包青天。在这部电影里,蔡文玄创造了一位精明正义的马来刑警角色,他受托侦察一系列神秘的罪案,其中还涉及含冤而死的鬼魂。至于《Jiwa Lara》(1952年),其故事情节与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里的“黄梁一梦”颇为相似。
另外,马来巨星比南利(P. Ramlee)大受欢迎的《Bujang Lapok》电影系列的原创故事也是由蔡文玄提供的。然而在他所写的剧本里,蔡文玄最初的构想只有一对父子,而不是三个“臭皮匠”(单身汉)。电影上映后证明这一题材的电影非常受到新加坡观众的欢迎,因此马来电影制片厂也乘胜追击制作了三部续集,并沿用类似的主题。喜剧三人组比南利、沙姆苏丁(S. Shamsuddin)和阿齐兹·萨塔尔(Aziz Sattar)亦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银幕明星。另外,蔡文玄也关注跨族群的爱情故事,尤其是战后的马来电影如《Singapura Di-Waktu Malam》(1947年)和《Selamat Tinggal Kekaseh-Ku》(1955年)中曾涉及这样的题材,因此他大胆撰写类似的故事,其代表作便是《Sri Menanti》(1958年)。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马来姑娘花蒂玛(由著名的马来女演员蔡彤饰演)和一位华裔青年王乐音(由香港演员张冲饰演)之间的爱情故事。电影里设置了一段三角恋,由香港新晋女演员唐丹饰演的少女美娣,和村长的女儿花蒂玛同时都爱上了男主角,但三人皆无法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同时期由国泰机构出品的《娘惹与峇峇》(1956年)以及由光艺出品的《血染相思谷》(1957年)等影片中也有类似跨族群相恋的情节,但蔡文玄的作品依然有其原创意义。
3. 诗人、填词人、电视编剧
除了撰写马来电影剧本,蔡文玄也曾为张莱莱的电影《马来亚狂恋》(1963年)作词,歌名乃南洋水果《红毛丹》,以一对男女对唱的方式,描绘了情侣之间的俏皮对话,并在其中穿插了新马特色美食,如甜品摩摩喳喳、米暹、椰浆饭、乌打等。当时,张莱莱原先的计划是邀请著名新马音乐人上官流云为电影写歌,可是他花了三天的时间在马六甲仍无法获得灵感,只好转而邀请蔡文玄帮忙。张莱莱在筹备电影剧本时,原本打算邀请1961年在南洋大学执教的“鬼才”小说家徐訏撰写,但后者表示自己在南洋的时间并不长,写不出贴近新马现实的故事,因此鼓励张莱莱自己尝试创作剧本。有趣的是,徐訏也是蔡文玄的朋友之一,曾为他的诗集《十二城之旅》写过序言并对他的诗歌风格极为赞赏。
蔡文玄以诗歌见长,并坦言其诗歌风格受到吴江左的影响,且主张新诗应该重视“韵”的使用。他出版过的诗集有《十二城之旅》、《无色的虹》、《雪泥》、《旅心》等。1978年,《无色的虹》获新加坡国家书籍理事会颁发的诗歌组书籍奖[8] 。1988年,该书被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提名东南亚文学奖,蔡文玄因此受邀出席在泰国举办的颁奖典礼[9]。在那里他与泰华文学协会的成员会面交流,也提议开展两地的文学活动,促进新加坡和泰国作家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当时蔡文玄建议将两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当地语言让读者能进一步认识这些作家。他极力推荐将泰国作家Nikom Raiyawa的小说《Taling Soong, Sung Nak》(1984年)翻译成中文,供新加坡的读者阅读[10] 。
难能可贵的是,蔡文玄不仅热心推动文学及翻译,他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文艺具有教育群众的使命”[11],由此可见,蔡文玄的马来电影剧本及文学创作(诗歌)皆贯穿了一种教育大众的理念,甚至是1980年他为新加坡电视台撰写的《灯蛾》剧本,同样有劝俗警世的作用。通过刻画一个富裕家庭成员间的财产纷争,蔡文玄展示了“贪婪爱利的人[犹如]扑火的灯蛾,最终必引火自焚”[12]。这是一部13集的彩色电视剧,也是电视台首部中篇电视剧制作,并由他的儿子蔡萱担任该剧导演。
4. “跨界”文化人
在南洋,尝试跨媒介/“跨界”创作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李星可(1914-1996)虽然在报馆担任编辑之余,曾尝试写过广播话剧《钓金龟》[13],但更多时候是以报人或翻译广为人知。例如1967年,香港的海尼曼教育出版社便邀请李星可完成13篇马华短篇小说的英文翻译,小说的作者包括林参天、苗秀、韦晕、絮絮、姚紫、李汝琳等[14]。海峡华人社群当中也有跨越绘画与歌舞剧的代表,像是被称为新加坡“本埠美术界之能手”的刘开赏(1889-1982)不仅开设了自己的画室,后来也成立马来歌舞剧团,并担任团里的编剧兼导演[15]。然而,像蔡文玄那样游刃有余地从事不同媒介的创作者十分罕见,他最初下南洋从事教书与编辑《电影圈》、《娱乐》的工作,后来和友人在新加坡的当店巷开设画室,二战结束后也创作马来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填词及诗歌创作,蔡文玄便是以他“跨界”的各种创作建立自己在新马的名声。
“跨界”人物在南洋的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和20世纪海外华人主动选择从事跨国移居、跨域活动有关,是其在与“近代殖民政权、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和国际资本主义”之间互动的策略,并试图创造“第三种文化”[16]。同时,有学者指出社会在迈入21世纪后逐渐出现经济一体化,中国无论是以“中华文化”、“大众文化”还是“一带一路”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甚至由于文化互动而形成的新的身份认同,无不让一部分人感到惴惴不安。这一现象不仅对华侨、华裔、华人的生活及其居住的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影响海外华人相关议题的研究方向,例如多元文化、华人性(Chineseness)、中国软实力等。正因如此,笔者认为 “跨界”/跨媒介的尝试,除了让我们能够看到经济与其他制度性的因素如何影响海外华人社,也能从文化的角度让我们理解“南洋”这一区域独特的社会面貌与特征究竟是如何被打造的。
[1] 南海影片公司地址在当店巷(克力路)53号之一。参考<广告>,《南洋商报》,1926年11月26日,页 9。根据李云的考证,黄敬一、郑超凡原先在南洋影片公司内负责办理暹罗和缅甸两埠事务。黄敬一离职后组织南海影片公司,又设立上海海维公司,专门经营国产影片运销中外各埠,并接受曼谷陈士影片公司、新加坡浪花公司和厦门影片公司等公司委托经营国产影片业务。李云的文章<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研究——我国早期电影发行托拉斯化经营的尝试>,收录在在2023年《当代电影》第12期。
[2] 新加坡印刷业曾经由广东商人主导,记录显示1940年代有30多家印刷公司,这些公司共雇用了1,000名工人。每家印刷公司的平均月收入在3,000至4,000元之间,而每位印刷工人的工资为20元。印刷所需的材料主要从挪威、芬兰、英国和德国进口,而荷兰、瑞典、美国和法国也是印刷原材料的供应源头。新加坡印务同业公会于1937年成立,当时有26家公司注册成为该公会的成员,但经营印刷公司的海峡华人社群则没有成为该公会的成员。这些由海峡华人经营的公司包括Jacks and Co., G. H. Kiat 和 Peter Chong。他们一般受理英文书籍和出版物的印刷。参考《星洲十年》 (星洲日报社,1940年),页627-629。
[3] 蔡文玄在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口述访谈(第 18 卷)中提到,他在华英戏院的工作十分忙碌。华英戏院最初可以容纳 680 人,在经过消防局的安全检查后,被勒令座位需减少至600个。平均入席率为60至70%,若适逢上映热门电影时,通常会出现满座的现象。
[4] 参考蔡文玄第17卷的采访。
[5] 关于曾几生和他父亲的生平,参考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 (教育出版公司,1995年),页 188-190。
[6] 青年励志社主要是提倡并推广青年文娱活动,他们也组织了其他团体,如中华语言统一促进会。有关青年励志社的详细介绍,可参考潘醒农发表在《南洋商报》(1979年8月5日、8月8日和8月12日)上的<青年励志社谈往>。
[7] 感谢杜汉彬和李彬铭与笔者分享关于《Kerana Kau》的资料与视频。
[8] 蔡文玄获奖的诗歌最巧妙之处乃借用马来词汇以展示新加坡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特征。这些生活化的马来用语言简意赅,不但反映了他的语言天分,也准确地反映蔡文玄想表达的意思。诸如 “kemari”(过来)、“terima kasih”(谢谢)、“mata”(眼睛,但也可以指警察)、“tolong”(帮助)和其他许多短语都是有意识地被嵌入他的叙事诗中,甚至能做到押韵,使人在阅读时更流畅顺耳。
[9] 蔡文玄在获得东南亚文学奖的肯定后,也奠定了他作为新加坡1980年代重要文学先驱的地位。参考 “Singaporean wins SEA Write Award”, The Straits Times, AFT, 1988年10月16日,页18。2000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内也设立了新加坡文艺先驱馆,介绍蔡文玄对新马文学发展的贡献以及他的生平事迹。
[10] 见 <柳北岸泰国获奖归来>,《联合早报》,1988年10月26日,页 42。蔡文玄曾通过1978年的“全国诗歌朗诵会”推动与其他新加坡非华族作家的合作,并邀请唐爱文、奈尔、马苏里、拉迪夫、维南和马卡山等人参与该活动。目的是通过诗歌朗诵活动,引起国人对文学的兴趣,进而鼓励人们尝试文学创作。唐爱文和马苏里也是东南亚文学奖得主之一。
[11] 参考<诗人与小说家——柳北岸与苗秀访问记>,《南洋商报》,1978年年月29日,页 3。
[12] 参考<本地制作连续剧 《灯蛾》>,《星洲日报》,1980年8月2日,页31。
[13] 参考李星可与《联合早报》的访谈,收录在https://interactive.zaobao.com/zaobao-centennial/oral-history/ly-singko.html。
[14] 该书名为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参考章星虹<翻译是一道桥>,《联合早报》,2020年12月14日。
[15] 参考张夏帏 <比先驱画家更早的先驱>,收录在2019年《源》杂志,第140期,页45-49。网络版,参考https://sfcca.sg/wp-content/uploads/2024/01/Yuan-140-1.pdf 。
[16] 参考Ong, Aihwa and Nonini, Donald (eds.),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